记者节 | 对话张志安:深度报道真的衰落了吗?

文 | 陆桂怡 沙兆杰
今天是第二十二个中国记者节,谷河青年就近期广受关注的深度报道发展的现状问题,专访了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张志安教授。
张志安教授研究方向为新闻生产、新闻从业者、新媒体与社会等。他长期深耕于深度报道实务教学和研究,著有《报道如何深入》、《记者如何专业》等“揭开真相”系列丛书,和《深度报道:理论、实践与案例》教材,发表多篇对深度报道和调查记者的研究论文。
在张志安教授看来,由于深度报道成本较高、互联网对报道时效要求更高等原因,与传统纸媒兴盛期相比,当下到达重大新闻事件现场的媒体记者数量与现场调查类深度报道容量确实在减少。但另一方面,一些垂直机构媒体的原创文章同样呈现了出社会的复杂性,提高了社会的可见度。作为当前深度报道的另一种形态,它们也拥有实质的公共价值。
“此消”:逐渐弱化的传统媒体深度报道
Q1: 在近期的热点事件中,有评论认为传统媒体在“得体地沉默”,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A1:我觉得不好这么说,中国发生的大事太多了,不能因为一个事情传统媒体没有介入,就说传统媒体都不作为,或者深度报道已经死亡。“得体地沉默”这个结论我觉得是很难成立的。此外,还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在中国,警方具有比较高的权威性,一般警方已经有调查结果披露的事实之后,媒体再进行调查时,这种调查已经很难突破警方的结论了,所以调查的余地相对来讲可能就没有那么大。
总之,我们不能根据一个案件,媒体是否去调查,就做出对整个舆论生态的判断,做出调查报道已死的判断。我觉得这种观点还是比较容易以偏概全吧。
Q2:您认为什么样的事情值得去做深度报道,什么样的事情不值得呢?
A2:凡是引发大家关注、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事件,真相又未明,都值得深度报道记者赶赴前方、奔赴现场。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一个事件媒体缺位,就说整个行业生态发生了质的变化。反过来,如果一系列事件当中媒体都缺位,我们就可以得出整个媒体行业生态在变化的结论。确实,现在重大事件发生之后,能够派到现场去的媒体相比过去明显减少,各家媒体去抢新闻的深度报道的态势其实是在弱化。一个事件不能看出全局,但是一系列事件中能看出今天奔赴现场实地调查的深度报道的媒体减少了,深度报道记者减少了。
Q3:像您刚刚说的,总体而言到现场去做深入报道、调查的媒体的确是减少了,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A3: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一个直接原因是成本。大部分传统媒体现在都没有深度报道部了。过去纸媒的盈利能力相对比较强,他们有比较强、比较大的深度报道团队,现在大部分纸媒的深度报道团队都被砍掉了,能保留深度报道记者的纸媒本身就不太多。我觉得,第一个原因还是跟传统纸媒的采访成本控制有关。
第二个可能是跟网络时代大家对采访速度的追求,和希望以相对比较低的采访成本来做出有一定关注度的报道有关系。不少媒体逐渐习惯于通过网络,比如说第一时间找到知情人通过电话进行采访。这样效率很高,人不用过去,又很快就能发稿。而且在热点事件的过程当中,这种比较“轻”的采访也往往能有较高的关注度。尽管这种采访,得到的信息是相对碎片化的,是单一维度的,但因为它是热点,有一定的关注度。
Q4:有评论认为,阻碍深度报道发展的最主要原因,是社会的苛责和不宽容在挤压着调查记者的生存环境,无论是报道内容怎么样写,记者总是会受到报道不全面、立场有问题诸如此类的指责,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呢?
A4:社会苛责当然不是主要原因,理论上,公众要求越高,可以促使报道更加专业。对专业媒体来讲,发表的深度报道如果涉及到纷繁复杂的网络舆论、多元的网络思潮,以及网络上相对愿意发表观点的群体,可能会因为立场和倾向上过于鲜明,或者是有一定的主观倾向而引发争议。一个好的报道总是很难讨好所有群体的,对记者和媒体来讲,要有面对多元舆论环境的心理准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需要通过报道去讨好哪个特定群体,还是以责任为担当、以事实为基础、以真相为追求。
首先,这涉及媒体所做的深度报道,更看重在大众舆论场中达成共识,还是在专业舆论场中得到认同。专业社群的肯定是基础,很难奢望在大众舆论场中获得普遍共识。换个角度看,对媒体而言,一篇报道引发争议,也往往说明这篇报道比较有影响力。
其次,对专业媒体来说,如果报道引发争议,过去这些年已经有不少应对经验了,应该采取透明性原则,可通过记者手记、媒体公告等公开回应方式,去针对这些争议背后的公众质疑进行说明。比如我们看到《中国青年报》2018年有一篇报道《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引发争议,比如有观点认为把一个发达地区的教育资源,通过视频直播方式分享给教育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孩子,这种做法只能让少数人受益,并不具有示范性。这时《中国青年报·冰点》采取的方法,是把很多他们微信后台收到直接受益的教育案例加以整理,直接“摆事实”给大家看。这就是今天媒体在复杂网络舆论环境中可能必需要做的事——不仅告诉公众新闻记者采访的“前台”,也要告诉公众作品生产的“后台”。当面对报道引发的争议,媒体和记者应该做好准备,真诚地跟公众沟通,说明报道过程和编辑部的态度。所谓的“透明性原则”既包含邀请公众参与,也包括向公众说明。所以,我不觉得所谓社会苛责是导致深度报道衰落的主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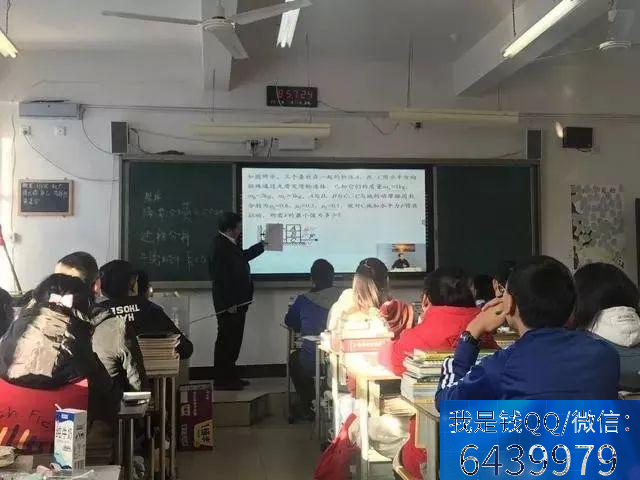
图源《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
“彼长”:蓬勃发展的随机新闻行动
Q5:近十年深度报道的业态变化是怎样的呢?
A5:移动互联网发展起来后,专业媒体的深度报道总体有所衰落。2012年,是传统纸媒从兴盛到衰落的一个拐点。近十年来,专业媒体因为成本、人力资源开支的压缩,深度报道的记者规模在大量减少。另一方面,互联网上的深度报道在兴起,特别是“垂直机构媒体”——大家习惯叫它们自媒体,但我觉得这样定义并不准确。像丁香园、兽爷、芥末堆等,这些垂直机构媒体的随机新闻行动,偶尔会针对重大题材发表深度报道或深度文章,影响力也很大。
此外,非虚构写作也是深度报道的一种表达方式,网易“人间”、界面新闻的“正午”,这些互联网平台中专业媒体人投稿或普通作者投稿驱动的深度报道正在兴起。所以,总体上看,互联网原创深度报道在增加,而传统媒体深度报道的规模在减少,直接从事深度报道的记者队伍在减少,由此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
Q6:2017年芥末堆发表了一篇《求职少年李文星之死》的原创文章,报道了李文星误入传销组织身亡的事情,这篇文章也引起了很大的舆论反响,但这是一个垂直的媒体机构,它并不具备原创性新闻的采编权,这样的一篇原创文章,为什么我们还是认为它是一篇深度报道?
A6:这里面最重要判断标准是,我们确定一篇文章是不是报道的时候,到底是看它实质的社会价值功能、报道样式,还是看采访主体是否具有原创性新闻的采访权?必须承认,没有时政新闻采访权,会限制深度报道的实践,但实际上,垂直机构媒体的粉丝多、影响大,爆料人、知情人或专业人士接受其采访时并不会太在意采访权的问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判断一篇文章是不是深度报道,主要看报道事实有否深度、报道题材是否重要,主要看其报道形态和社会功能。从这个角度看,不管是有采访权的界面也好,或者只是垂直机构媒体的芥末堆也好,他们所做的这些报道实质上都是深度报道。因为有原创的调查,有社会舆论的反响,有比较重要的新闻价值。不过,也必须看到,不管是芥末堆做李文星调查,还是兽爷做疫苗之王,还是丁香医生做权健公司风波的调查,这类实践可以称为“随机新闻行动”,这种报道对一个机构而言并不持续,主要是偶然为之,是在特定事件和话题情境下所做的调查报道或深度报道。

图源芥末堆官网
Q7:像您说的随机新闻行动,这类的互联网深度报道具有很强的偶发性,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间歇、偶发的深度报道,是否有力量去支撑 “此消彼长”的增长?
A7:我刚才讲的“此消彼长”,并不是以绝对的数量角度来做比较的。相对过去,传统媒体自身来讲,专业深度报道是“此消”了,而相对过去,这种垂直机构媒体的随机新闻行动的深度报道是“彼长”了。但是,这并没有绝对的数量上的比较。
如果是从专业媒体深度报道的量、规模和它的持续性来讲,传统媒体肯定还是比垂直机构媒体的随机新闻行动要大的多。比如,新华社的《经济参考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中国之声、《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财新传媒、《三联生活周刊》、《新京报》、《成都商报》的“红星新闻”等,这些专业媒体的深度报道数量,才是深度报道的主力军。
Q8:那么,这些随机新闻行动会有什么侧重的报道议题吗?
A8:好像没有特定的规律,因为是偶发性的。要根据这个机构当时抗风险的能力,写作者当时的采访便利。实际上,机构媒体中很多人是从专业媒体转型过去,他们有一个好处就是采访对象的人脉积累和扎实的采访能力。
垂直机构媒体的写作者在一个专业社群里面能比较方便地找到采访对象,比如对丁香园、丁香医生的用户群体来说,很多都是医疗机构的从业者。这些专业人士作为受访者,并不因为你是不是专业媒体而考虑接不接受采访,而是看你报道的内容有没有价值。对芥末堆的采访对象等案例来讲,他们是相对弱者,没有其他发声渠道,作为草根阶层,会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来引起关注和动员社会。弱者当然不在乎你是专业媒体或垂直机构媒体,他们在乎的是你能不能帮我。
第二点是这些写作者会有自己的人脉,能想方设法找到相关人士。偶发性的采访,本来就不是规律性的或不可持续性的,每做一篇特定文章的时候,写作者总是必须找到一定的人脉关系。举个例子来讲,有一家传媒类的公号,经常会采访新闻传播学界的学者,谈一谈对一些传媒问题的看法。大家都知道它不是一个专业媒体,但是并不介意,因为会有传播量、粉丝、影响力。
语境转换:从新闻传播到公共传播
Q9:如何看待随机新闻行动生产的内容的价值?
A9:还是要从社会价值或公共价值的角度去看那些偶发性的文章,到底有没有价值?当然还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增加了多元事实和复杂真相的供给,所以对受众、对社会、对国家还是有好处的。
比方说《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大概是2018年2月份在网上发出来的,是一个当事人自己做的一个非常长的记录,这个文章引发了大家非常高的关注。后来,财新传媒等一些媒体都围绕它去做后期的关于医院转诊情况的深度报道。
可见,有时候,一个事件亲历者的自述和记录,也比一个记者去写调查报道有更强的代入感、现场感甚至会在议程设置层面发挥更大的价值。第一,那篇文章让很多人触动,觉得医院的转诊制度是存在一定缺陷的。第二,对中产阶层来讲,如果个人没有买重疾病的保险,突然间碰到家庭有人面对生命失去的风险,可能会带来极大的压力,中产家庭的安全感就很容易被打破。像这样的文章,尽管我们不把它叫做所谓的“报道”,但这样的深度文章发挥的社会功能跟深度报道是一样的,也是在记录和解释问题,在呈现真相。
我记得前几年还有一位经济学者,到江西的余干县去过节,发现余干这个地方是贫困县,但消费却非常活跃。他就写了一篇自媒体文章,专门去讲他在当地所做的临时调研,那个调研文章其实就是一篇深度报道,完全可以放在《南方周末》经济版等专业媒体上。他有采访吗?他没有媒体的那种采访权。可是他根据自己的经历,也可以来做调查,进行复杂事实的披露。这些都增加了我们社会的能见度,把复杂性呈现在公众面前,所以都有价值。
Q10:所以它其中蕴含的公共价值其实更为重要。
A10:今天,我们其实换了一个语境去看深度报道。过去我们是从新闻传播的角度去看深度报道,今天我们恰恰需要从公共传播的角度去看深度报道。网易“人间”这样的栏目,它其实为写作者的自我记录提供机会,里边也有人在采访或调查,比如一个退休警察,一个曾经的少年犯。这些非虚构写作的方式跟《南方人物周刊》没有本质区区别。
Q11:刚刚您说随机新闻行动其实还是由原来的专业记者转行过去的,那么对比传统媒体的深度报道,您觉得互联网的原创新闻报道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A11:第一,少数垂直机构媒体,所做的网络原创深度报道,有个典型特点是社会连接(public connection),它往往通过一个小的故事去连接到一个大的问题。
第二,它一般都会有符合网络传播的情感趋势,把个案的故事写得比较悲情或打动人心,这样更加具有情感动员的作用,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阅读、情感共鸣和大量转发。
第三,这些文章叙事的时候,往往不会像专业媒体的原创深度报道那样,特别追求所谓的信源平衡。有时,因为采访的难度,其信源平衡可能没有那么强,往往会更注重故事性、动员的情感传播特点和对动员效果的考量。从信源的平衡处理,调查的扎实程度看,可能就没有专业媒体这么强。

《报道如何深入》(张志安 著)
Q12:您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深度报道30年:轨迹回望与专业反思》,提到每个年代深度报道都有它因时而变的特征,比方说80年代可能是偏向启蒙,90年代功能逐渐转向了监督,新世纪则转向了记录。是不是可以说,深度报道在不同的时代,实际上都有着自己的活力和特征?
A12:是的,需要补充的是,当下还有个重大挑战是所谓的“后真相”,相当一部分公众好像对情绪或碎片化的信息会更在意或者更容易产生激动情绪,对复杂的事实或事实背后的真相好像又没有那么在乎和期待,客观上来讲,这对深度报道行业提出了新的挑战。
大众还是要坚持“事实胜于雄辩”,通过媒体深度报道了解事实真相,在事实清楚、真相接近的基础上做出判断、达成共识。重大事件发生后或重大舆情出现后,记者仍需奔赴现场,媒体仍需深度报道,公众仍要敬畏真相,这样才能在满足公众知情权基础上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积极推动社会进步。
-END-
排版 | 王江壕
编辑 | 施毅敏
初审 | 刘颂杰
复审 | 钟智锦
终审 | 阮映东




